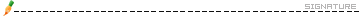乡下人、城里人,相同的生命不同的价之(一)
一、法律明文规定:城里人贵、乡下人贱
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该法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为配合该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实施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进行规范, 于2003年12月4日通过并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不再直接规定赔偿的数额和种类,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该法与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相比,在死亡赔偿标准上,原办法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赔偿10年。就是说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受害人在哪个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就按哪个地方的平均生活费计算,存在的只是地区差异。而新的解释,对死亡赔偿标准,除了时间上从10年延长到20年,更为明显的是,对死亡人的身份也进行了划分,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以《广东省200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深圳城乡赔偿额最大差额高达80余万。
按该标准计算城里人的死亡赔偿标准为:
1、丧葬费:1.62万元。
2、死亡赔偿金。按照深圳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20年,共计57.33万元。
3、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深圳的标准是每年2.12万元,对于未满18周岁的人赔偿到18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按20年计算;年满60周岁的被抚养人,每增加1岁,赔偿年限少1年,75周岁以上的,赔偿5年,这一部分最高赔付可达42.37万元。
以上三部分相加,共计101.32万元。
乡下的的赔偿标准:
1、丧葬费, 1.62万元。
2、死亡赔偿金,按照上一年度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20年,总共是9.38万元。
3、是被抚养人的抚养费,按照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一年是3707.7元。对未成年人抚养至18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的赔偿20年;被抚养人60周岁以上的,每增加1岁,抚养的年限减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抚养费最高赔付可达7.41万元。
这三部分总和是18.41万元。
简单加减,深圳城乡居民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标准最大相差82.92万元。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全国各省市都相继颁布了相应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规定了四级数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而且乡下人城里人的数字都有明显差异,例如:
《上海市2006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规定:准
1、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8645元;
2、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13773元;
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342元,
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7265元;
《天津市2006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规定:
1、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3元;
2、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9653元;
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202元,
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3590元;
其中《广东省200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是最为复杂,该标准是这样规定的:
1、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年) 计划单列市 深圳 28665.25 元,经济特区 珠海 18907.73 元,汕头 12229.17 ,一般地区 14769.94
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年) 4690.5
3、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元/年) 计划单列市深圳 21188.84 元,经济特区珠海 14323.66 元,汕头 9505.66 元,一般地区 11809.87 。
4、 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元) 3707.7
自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此乡下人、城里人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就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定下来,乡下人城里人同命不同的不公平现象的合法化,引起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争议和讨论。
二、同命不同价历史渊源?
不知什么时候,中国有了乡下人、城里人概念和区分,多年以来中国人对乡下人城里人的划分似乎也习以为常了,但是中国人同命不同价却是自古就有的现象。
根据吴思的《血酬定律》引用的史料,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 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纪、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42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西藏噶玛政权(噶玛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达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
从上可以看出,生命自古就有价,而且生命的价格因人而异,同命不同价是一种历史现象,现实中在处理交通事故的乡下人城里人的不平等现象是某种历史现象的继续。
三、立法的缺陷与司法的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开宗明义(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随后和的条文中对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劳动权等等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对公民的“生命权”与“身体权”没有作具体的规定与阐述。
所谓生命权,简单地说,就是“活的权利”或“生命安全的权利”,它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非法剥夺的权利。
身体权指公民维护身体形态完整和因身体存在而产生的其他身体利益不被侵害的权利。
虽然要求将“生命仅”与“身体权”的保护入宪的呼声早就有之,但是无论学术界还是立法界对此似乎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在实践中势必就会出现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显是偏重于保护城里人的利益。乡下人开车撞了城里人按城里人的标准赔偿,城里人开车撞了乡下人按乡下人的标准赔偿,如此就以能引出以下几个问题来:
1、该《解释》似乎明显地是在保护有钱人的利益,似乎我们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已经不敢得罪有钱的人,也没有能力得罪有钱的人了。
2、面对历史和现实,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屈从了传统的力量还是财富的力量,也不能不打个大问号了。
3、再说白一些,城里人乡下人在死亡面前都不平等,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平等的?
4、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立法、司法的理念与立法、司法技术也似乎距离时代的要求太远了些。
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违反宪法的,与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相对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后,在中国土地上出现这样的法律,上对不起先烈下对不起子孙。
四、现实中的困惑与突破
立法上的缺陷,观念与技术上落后必然会带来现实的困惑,为此执法与司法机关也一直在寻求突破,以求得“良心”与“良知”的安宁。
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在即使车祸中的死者是农村户口,如果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工作和收入,那么他要按照城镇户口的标准进行赔偿。
今年5月1日,2006年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开始执行。该标准规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交警部门将根据事故受害者从事行业及其所在地的平均收入为标准,核算交通事故责任者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金数额。以死者生前职业作为死亡赔偿的计算标准,较之过去受到公众强烈质疑的“城乡二元分法”,在赔偿的“等级观”上无疑是更进了一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于日前发布了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来自农村的事故受害人要按照城镇居民生活标准计算赔偿标准,首次实现农村人与城镇人“同命同价”。
重庆市高院可能会在今年出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指导性意见,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并且达到一定年限的农村居民,其损害赔偿标准有望和城镇居民一致。
2004年11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终于制订出了新的《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办法》及《二00四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新的办法取消了死亡赔偿金按盟市、城乡区别标准不一的不平等规定。明确规定“ 死亡赔偿金按照自治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照二十年计算”即取消农村人口按农牧民纯收入计算的缺陷,而且是“自治区上一年度”,不是过去按盟市划分了。除此之外,本《办法》中各项指标均采用了“自治区”平均标准。
另据来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18日《成都打破交通事故“同命不同价”》报道,在城市生活10年之后,农民邬世荣不幸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法院近日作出判决,认为邬世荣虽是农村户口,但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没有差异,应按城市居民的标准获得赔偿,一进城农民车祸身亡按市民标准获赔30多万元。
就社会上对于“同命不同价”现象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宣传处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司法解释经过这两年的司法实践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对“同命不同价”比较关注,法院也了解到此情况,并且近两年来都在做这方面的调研。但在短期内不会作出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回答媒体关于“同命不同价”问题之时曾表示,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我们希望,这一过程能够尽量快一点。
但就是如此社会各界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的非议与质疑声依然不断,要求议全国人大废止或责令最高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司法解释的呼声不断。
五、非议和责难声引发的警示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引发城里人、乡下人的标准之分和之争,以及在立法、司法界的混乱告诉了我们什么?
1、死亡赔偿是象征性的还是实在性的?无论如何,对死亡的赔偿都是象征性的而非实在性的,因为生命是无价的,不可以赔偿的。既然是象征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可以有统一的标准,甚至可以没有地区与地域的差异。
2、赔偿是对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是与其能创造财富的能力有着必然有联系,甚至就是对应关系,其实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死亡面前也一律平等,人死以后所有的能力都归于“0”,赔偿仅仅是对死亡者的家属进行精神上的补偿为基础,而非以物质上的补偿为前提,法律上规定的金钱补偿仅仅是象征着对死者家属精神上承受的痛苦进行补偿,这种补偿原本就不能因人而异,因为人的生命是平等的,死亡给家属亲人带来的痛苦依然是平等的,没有质的差异,对一个没有质的差异的事件居然要以量的差异来显示公平,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3、法律确认个人出生和身份至今能为人带来地位和财富的差异的合法性,无异于认可了古老的等级制度的合法化,这是我们需要的法律制度吗?
4、在中国城里人和乡下人相比,还是乡下人多,城里人少;有钱人少,没钱的人多,立法与司法是看谁的脸色,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有钱人还是没钱的人?
说白了,要把城里人乡下人的死亡赔偿标准统一到一个标准下,不是降低城里人的赔偿标准,就是提高乡下人的赔偿标准,或者再制定一个新的标准,这原本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却被人为的复杂化、庸俗化、功利化、势利化。
从以上四个问题不能看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界落伍时代太久远了,总是以落伍的观念与方法来解决新问题,所以我国立法界与司法界的观念亟待更新、技术亟待改进,尤其是对人生命权与身体权的认识有待于快速提高。
邱旭瑜律师(天上的虫子)
2006年8月6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