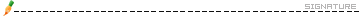这件事情很快在明廷炸开了锅,于是是否接受把汗那吉的投降,朝野意见分歧相当之大,很多人认为,把汗那吉区区数人投降,留之无益,反而会引起俺答的报复性攻击。当然,也有人是力主受降的,比如王崇古,他向隆庆皇帝做了一个很不错的计划性阐述,说服了隆庆皇帝接受把汗那吉的投降。
隆庆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认识倒也清醒,在和高拱张居正商议后,皇帝和两个人内阁大臣一直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益的,但是外面那群言官可不管你们里面是怎么商议的,雪片般的反对奏疏飞了进来,让性格温和的隆庆皇帝勃然大怒,忍了你们这么久,在其他的小事上唧唧歪歪也就算了,这种军国大事也不分青红皂白,于是他把带头的言官连降两级外调,以做惩戒。而外廷,内阁和兵部有很多是支持皇帝的意见的,所以这股反对浪潮也没能形成气候。
果然,事情的发展都在王崇古的预料之中。把汗那吉的祖母一克哈屯很想念这个孙子,每天找俺答哭诉,俺答无奈,自己又觉得实在有负把汉那吉,于是带领十万大军准备到大同抢人,虽然他明知道可能不是明军的对手,但是不管怎么说也要硬着头皮上了。
王崇古等的就是这一天,他立即派人去和俺答谈判,希望俺答认清形势,双方可以商量议和,只要俺答可以交出汉奸赵全,明朝可以把把汗那吉奉还,双方可以和平相处。俺答知道自己凭借武力根本没有能力攻下明军防线,所以对议和的条件喜出望外。于是双方很有诚意的坐在一起就和平问题展开了会谈。
蒙古人屡次侵犯边关,所图无非是中原地带丰富的物资,所以俺答在谈判的时候提出希望和明朝通供互市,以后双方永不再战,自己愿意接受大明天子的册封。
这个问题明朝需要政府进行商议,但是议和的谈判进展的很顺利,隆庆皇帝果断的答应了前方的谈判条件,允许把把汗那吉奉还。一克哈屯见到了孙子,喜极而泣,俺答知道自己有负这个孙子,也表明了悔意,祖孙三人尽释前嫌,抱头痛苦。俺答当即向明朝使者表示,自己非常感激大明天子的恩情,愿意世世代代臣服大明,发誓永不犯边。
让明朝人痛恨不已的汉奸赵全等人,被押赴北京,隆庆皇帝亲自参加了献俘典礼,可见举国上下对这群出卖本民族利益的汉奸的痛恨,典礼结束后,汉奸们被揪出紫禁城,公开处决,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汉奸永远是汉奸,永远是人们唾弃的对象,即便政权转换岁月流逝时代变迁,他们的行为也应该为人所不齿!
下一个头疼的事情就是关于是否允准和俺答通贡互市的争论,明朝的大臣再一次展现了他们七嘴八舌的本领,言官有人上疏反对,认为鞑靼人言而无信,开市后必定借机寻衅,大肆抢夺。隆庆觉得他们的话也有道理,因为信誉的问题谁也不敢保证,而以前俺答的信誉记录是比较差的,所以要求群臣进行廷议给他个结果。
兵部集合了各部府院科道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廷议,最终送上来了结果让隆庆皇帝很郁闷。大臣们明显分为了两派,以定国公徐文璧为首有二十二人赞同通贡互市,英国公张溶等十七人表示反对,另有五人只同意通贡不同意互市。本来皇帝是想让兵部自己根据各方的陈述拿个意见上来,但是兵部尚书郭乾是个军事专家,对政治和谈没有一点决断能力,就直接把大家的言论堆积上来送给隆庆,如此大的意见分歧摆明了是把皮球踢给了隆庆皇帝,这个时候只能是皇帝自己下决断了。
终于在隆庆五年三月初八,皇帝亲自下令执行和鞑靼的通贡互市协议,允许册封俺答为王。
同年五月,明朝使者与鞑靼人商定了通贡次数和互市地点,朝廷与蒙古人在大同城外进行了俺答受封典礼。隆庆皇帝赐给俺答蟒衣一件,册封俺答为顺义王,授予俺答亲属部下各个官衔。顺义王遥望帝京,拜谢“大明仁圣皇帝陛下”,发誓“臣弟侄子孙世世感戴恩德,不敢背叛”。
明朝与蒙古两百年来的互相征战,终于在隆庆皇帝的治下告一段落,从此以后,草原上的硝烟少了很多,两个民族之间几乎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征伐事件,而明军北方边事再起的时候,对手已经换成了另外一个民族了。
这个懒皇帝。在位只有短短的六年,但是正是在他这短短的六年里,明朝的边患“南寇北虏”都被他逐渐解决,明朝在盛世之后从未有过像他这样的大好和平环境,这个环境为以后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基础,但是可惜的是,这个聪明的懒皇帝却并没有能够享受到他的这一伟大成果很长时间。
帝王之路的尽头
明朝的皇帝习惯了被人挑毛病,有人说明朝的皇帝昏君多,其实问题在于他们看人的眼光,如果一个人盯着一个朝代的皇帝全看他们身上的缺点,那几乎这个朝代就没什么好皇帝了。而全看他们的优点,那么昏君都能被吹的英明神武,比如明清两代的皇帝就有这些截然不同的境遇。
一个人的缺点是很好找的,比如明朝的皇帝英明如太祖成祖,那可以说他们残暴;勤奋如崇祯,可以说他愚蠢;专情如成化,可以骂他懦弱;精明如万历,可以说他懒惰。文武双全如宣德,可以指责他爱斗蟋蟀;叛逆如正德,那可以骂的就更加多了。最让人佩服的是自身修养接近完美的弘治,被指责迷信佛教和惧内纵容外戚,当然我们对比一下连咸丰抛弃京城逃命都被说成是聪明的表现,那所谓清朝无昏君也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这位隆庆皇帝除了懒之外好象也没什么缺点,而且他的懒和他儿子比起来也不值得说,那么,他被大肆宣扬的缺点是什么呢?是好色!
这个话题其实也怪不得现在史学家,因为这是当时的明朝言官挑起的。隆庆皇帝确实本身比较好女色一点,当年他身为亲王的时候,在王府受到父皇的压抑,这个二十多岁的藩王,没有就藩的机会,也不能当太子,至于以储君身份参与朝政,那就基本想都别想了。所以除了按时去听他的老师们给他上课,他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在自己的王宫中和女孩子进行消遣。他的遭遇,和他后来的孙子明光宗朱常洛倒也挺相似。
但是作为贵族的身份,身边的女人多了些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人之常情,何况他是亲王,储君甚至是皇帝。明朝言官的特点就是喜欢把一件很小的不好的事情,宣扬成像天那么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明朝的厂卫制度一直为人所诟病,这里面就有明朝言官的功劳,他们从内心底是鄙视太监和特务机构的,所以这些人和机构只要一冒头,文官们就竞相打压。明宪宗成化年间,皇帝从其他部门调集了几百人组建了西厂,意图提高这些特务机构的办事效率,这件事情在明朝朝野就炸开了锅。西厂才成立几个月,只是单单办了一点案子,言官的上疏就已经把他们形容成搞的朝野上下恐怖异常血流成河,又有人说西厂派到下面去的特务们什么都管,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连邻里吵架夫妻矛盾他们都知道并干预。这些东西就说的实在信口雌黄了,西厂的建制一开始就那么几百人,全部派下去一个州府分一个都不够,居然能把全国都监视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所谓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无论是科技手段还是人员规模都比所谓的西厂不知道大了多少倍,人家那么多人连个本拉登都找不到,西厂的特务们莫非是神仙?在文官们强烈的抵制下,才成立了几个月的西厂又不得不被撤消。
所以很多事情一经言官渲染,就基本变味了。
隆庆皇帝的原配夫人姓李,是在裕王府中娶的,她为朱载垕生下过一个儿子,但是母子两个人实在命薄,一个没有皇帝命,一个也没有皇后命,两人双双在隆庆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病逝,隆庆对这个夫人的死感到非常的悲痛。他续弦的夫人姓陈,后来成为了隆庆皇帝的陈皇后。
这位陈皇后最大的悲哀在于一直没有一个儿子,但是隆庆皇帝似乎并不以为意,从来没有动摇过她的皇后地位。感受过没有亲情之苦的隆庆,的确比他的父亲更加注重亲情,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要比嘉靖要好的多。
排名在陈皇后之下的妃子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李太后,万历皇帝的生母,当时是李皇贵妃。这位李贵妃其实是一个侍女出身,当年朱载垕在裕王中穷极无聊,偶然发现了这个貌美的侍女,就临幸了她,很幸运这位侍女很快就怀孕了,这个孩子成为了隆庆皇帝在世的长子,嘉靖皇帝的长孙,未来的万历皇帝。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隆庆皇帝对这个女人只是一时的兴趣,因为在生完长子朱翊钧之后,李贵妃还生了隆庆的另一个儿子。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李贵妃的儿媳,也就是她孙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氏也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是万历皇帝对这个女人就明显不像他父亲一样那么上心了,完全是一时的兴趣。后来为朱常洛的太子之位争论,李太后去问万历为什么不立太子,万历随口说了句他是宫女的儿子,李太后听了大怒,大骂万历说,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李贵妃有两个儿子,而陈皇后一个都没有,这就难免会令人觉得皇后会失宠,这种庸人自扰的话题其实明代的言官们最感兴趣,他们就像今天的狗仔队一样密切注视着深宫中所发生的一切。云南道监察御史詹仰庇(这个名字起的真是妙)就是这么一名合格的“狗仔”,有一天,他在路上偶遇刚从宫中出来的太医,就连忙上去密切打探宫中的情况,太医告诉他,说皇后最近病重,已经从坤宁宫里移居别宫了。
詹仰庇就像得到了独家头条,立即拿起笔写了奏疏,指责皇帝虐待皇后,说皇后得病一定是皇上耽于声色,不理甚至虐待皇后,并且还指责皇后移居其他宫中是被皇帝逼的。
这个奏疏自然不止是只呈送到皇帝面前,它立即就传遍了朝野上下,言官们一看,大家顿时来了精神,像上文提到的劳模型人物骆问礼,就对皇上和皇后的感情问题大发议论,指责皇上对皇后不好,又指责皇帝过于好色,其他言官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不知道事实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很明显,詹仰庇所写的东西,大多出于他自己的臆测,几乎没什么是他确定的证据。隆庆皇帝拿到这些骂他的奏疏,可以想象自然是哭笑不得,他给出的理由是,皇后身体不好,换个地方住有利于调养她的身子,你们这群家伙又不知道宫里的事情,不要废话,看你们无知,我就不追究了。
但是朝野上下对隆庆皇帝的好色几乎是一致认定了,连外界都一致认为皇帝好女色,还发生欺诈事件。有个太监叫张进朝,诈称自己要替皇帝到湖广去选妃,外界信以为真,连忙有女儿的拼命嫁女儿,也不管是什么人家了能嫁就嫁出去,生怕自己女儿被送进皇宫,天人相隔。后来才发现是假的,这个太监被处斩。
于是后来的隆庆皇帝就惨了,什么事都能被联想到女色上面,有一次,礼科给事中蔡汝贤给皇帝上疏,大致的意思是,臣前几天为皇上导驾,私下里看皇上觉得皇上比以前好象瘦了一点。皇上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的,自己一定要加倍珍惜,所以臣希望皇上以后对女色要慎重,每天没事的话就阅读一点经史,亲近学识渊博的大臣,不要再沉溺于女色之中。
几句话把隆庆说的郁闷无比,想不到自己瘦了也能被拿来说一番事。自己好色的确是事实,但是哪个皇帝不好色呢?有些人好个女人连江山都丢掉了,自己从来没有为女人而耽误国事,所以他自己觉得和女人待的时间长一点与履行好皇帝的职责根本是两码事。
但是隆庆皇帝这个冤屈估计是永远也洗脱不了了,他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很快给言官了落下了口实。隆庆六年春,三十六岁的隆庆皇帝病倒了,大家一直认为皇帝的病是由于过度纵欲,经过数月的治疗,皇帝的病一直在恶化,群臣们意识到,也许是应该到安排后事的时候了。
其实明朝的大多数皇帝,都没有能够活到四十岁,有很多人认为纵欲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因素,明朝死的最早的皇帝是天启,二十四岁,但是这个皇帝在性上面没有什么过多的爱好,而只有一个皇后的弘治,同样也是只活到了三十多岁。而活的比较长的人如太祖,嘉靖和万历,在女色方面并不见的比那些死的早的人差,尤其是朱元璋临死前几年还制造了不少小生命。
隆庆皇帝的儿子只有十岁,像宣德皇帝一样,他对这个儿子非常的喜爱,但是又很不放心,他的国家只能寄托在高拱,张居正身上。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皇帝病危。三位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和新近才入阁的高仪慌忙来到乾清宫,他们看到的皇帝,已经在床上奄奄一吸,皇太子立在身旁,陈皇后和李贵妃避入惟中,司礼太监冯保向他们跪宣了隆庆皇帝的顾命诏书。
三位大臣号啕大哭,在李贵妃的劝说下,才打起精神,草拟了皇帝的遗诏,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将接替他父亲的位置,成为大明王朝新的皇帝。
第二天,年轻的隆庆皇帝驾崩在了乾清宫,一切都与他无关了,二龙不相见的魔咒,内阁的争斗,言官的聒噪,俺答的骚扰,女色的诱惑等等等等,都随着他生命的消散化做尘土。也许他还放不下自己这个大明帝国,但是这个爱好悠闲生活的天子应该不会这么有责任心的在临死之前都放不下这一切,他应该觉得自己完成了上天给自己赋予的皇帝这一职责,至少在在位期间,他没有辜负这个工作,也许唯一遗憾的,是自己没有能够多撑几年,为国家留下一个年长的君主。他的儿子,聪明伶俐,当了大明皇帝之后究竟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他永远也看不到了。
历史其实很是难说清的东西,有人说,如果隆庆皇帝不是那么早就去世,那么张居正永远也不可能主导一场他后来实践的改革,有人说,如果隆庆皇帝死的晚一点,他可以把万历培养的更加好,也有人说,如果他还继续活着,明朝说不定能够走的更加的好。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其他的东西谁又能知道呢~
总体说来,他是一个出色的皇帝,他的皇帝生涯最出色的地方在于,他摆正了皇帝的位置,所以他没有亮点,他不像其他的皇帝那样有那么多的故事吸引人。我们几乎不能从他身上找出多少有趣的话题,但是单看他的政绩是出色的,不喜欢他的人,除了拿他的道德和性格来说事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能找的出来的理由了。不知道隆庆是否喜欢他现在在历史上的地位,默默无闻,于人无争,也似乎正是他性格的体现。
有人说张居正完成了大明朝的中兴,其实这个中兴的基础,有很多是要归功于这个懒皇帝的,他提拔了高拱张居正,发掘了很多人才,留下了一个精英政府,缓和了边疆冲突,开放了海禁,为张居正的改革复兴提供了基础,而他当皇帝的时间,只有区区的六年。
他被上庙号为穆宗,布德执义曰穆。
公元1572年,大明王朝的第204个年头,第十三个大明皇帝坐在了宝座上,他还不足九周岁,但是这个孩子已经是中国的最高首脑,开始他四十八年精彩纷纭的皇帝生涯,他比他的父亲的确精彩多了。
其实对于高拱的《病榻遗言》,我本人并不是很喜欢引用上面的资料,因为觉得高拱这个人太小气,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抬高自己打击张居正之嫌,比如在张居正联合冯保扳倒高拱的斗争中,把张居正刻画的过于无耻。而在王大臣刺杀案中,高拱又以受害人的身份,指责张居正和冯保意图栽赃嫁祸以诛灭高拱全族。高拱的一面之辞实在让人无法对整件事情有一个清晰客观的认识,不过《病榻遗言》里的有些记述,看看还是很有价值的。
隆庆六年正月下旬,皇帝开始染病,并且在患病的同时身体还有热疮。医生给皇帝调理了整整一个多月,隆庆的身体才稍微有点好转。到了闰二月十二日这一天,隆庆感觉身体好了一点,于是挣扎着决定勉强去视朝(这对那些骂隆庆皇帝懒的人真是讽刺)。传召大臣们上廷的钟声立即响彻了紫禁城。
内阁大臣高拱和张居正也在听到钟声后立即离开内阁,匆匆赶去上廷面见皇帝。他们俩人走到会极门,已经看到隆庆皇帝的轿子停在那里,隆庆并没有坐在轿子上,而是艰难的往文华殿方向步行而去,脸上的表情似乎非常生气,而太监们却跪在皇帝的周边,这使的俩人非常迷惑,因为皇帝传召大臣的地方并不是文华殿,赶紧上前去询问。
隆庆显然也看到了他们,命令几个太监跑过来说:“皇上宣两位阁下。”
二人立即跑到了隆庆的面前,隆庆看见高拱,脸上的脸色变的温和了一点,他迈着艰难的步子,走到高拱的身边,一把抓住高拱的衣服,用力的抓着,想要说话。
高拱看到皇帝如此,数十年的朝夕相处让他体会到这位皇帝的意思,连忙说:“皇上为什么要发怒?这是想要去哪儿?”
隆庆看着高拱,缓缓的说:“我不想回宫了!”
高拱不明所以,看着隆庆虚弱的身体,只好劝慰皇帝说:“皇上不回宫这怎么行呢?希望皇上还是回去吧!”
隆庆面对着自己这个最心腹的爱臣,一向言听计从的他沉思了一会,然后说:“好,那你送我。”高拱连忙回答:“是,臣送皇上。”
隆庆松开了抓住高拱衣服的手,又抓住高拱的手,揭开自己的袖子,露出臂上的疮疤,说:“你看,我身上的疮至今还没有落疤!”高拱看了,心中不禁酸楚,隆庆突然又愤愤的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家有长君,是社稷之福!可是太子还太小。”
高拱感受到了隆庆对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绝望,连忙劝慰皇帝说:“皇上万寿无疆,何出此言啊?”
隆庆冷冷的回答:“有人欺负我!”
高拱疑惑的问道:“是什么人这么无礼,敢对皇上不敬?祖宗自有家法,请皇上告诉臣等,臣等必当依法处置。皇上身体刚刚转好,还是不要发怒,保重身体要紧。”
隆庆沉默了一会,淡淡的说:“算了,先生又不是内官,宫中的事情怎么会知道。”
高拱默然,也不敢深问,只好一路陪着隆庆回去。隆庆的手一直握着高拱的手,走到皇极门,突然说想喝茶,太监们立即奉上茶水,隆庆喝了几口,抬头看了看周围,说:“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了。”
高拱又陪着皇帝走到乾清宫,在皇帝的寝宫门面,高拱习惯性的停住了脚步,正拉着他的手的隆庆,回头看着他,简洁而又有力的说了两个字:“送我!”高拱不敢抗旨,随隆庆进了乾清宫,隆庆找了个座位坐下,却不放开高拱的手,和高拱随意言谈,谈着谈着,眼睛中竟然含有泪水。
这时内阁大臣张居正和成国公朱希忠也进入了寝宫向皇帝问安,高拱便与他们二人辞别皇帝守在门外侯旨。过了一会,皇帝把他们又都召了进去,隆庆默默的对他们说:“朕刚才有一点恍惚,自古帝王的身后事,大致都差不多,卿等仔细考虑一下吧。”
三位皇帝的近臣面面相觑,他们想不到皇帝已经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了,没办法,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领旨叩头,退出寝宫。突然有一个太监跑了出来,拉住高拱说:“请高阁老守侯在宫门外面,不要离开。”高拱说,那就他和张居正一起留下吧,隆庆允准了。
到了晚上,隆庆又下旨意要求高拱住宿在宫中,高拱认为有违祖制,便选择了住在西阙的太监住所,以防止皇帝的召唤。两位内阁大臣不敢回家,外面的大臣们自然谁也没心思回家睡觉了,全体留宿在了外廷。直到内廷传出消息,皇帝的身体好了一点,大家才放心回去。
这是一段真实的记载于高拱的《病榻遗言》的事迹,谁也没有解释过隆庆那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他事后也说自己当时的精神有一点恍惚,可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皇帝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和对自己这些大臣突然产生的眷恋,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了他的心头,他的内心有着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悲伤和对这个世界一切的眷恋,他的臣子,他的妃嫔,他的儿子等等等等。
数日后,隆庆的身体又好了一点,便带着病体亲自来到了内阁,看望高拱和张居正,隆庆扶起跪拜的二人,拉着高拱,仰望天空良久,欲语还休。高拱再次把皇帝送回了乾清宫,张居正发现皇帝的脸色很差,估计离驾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外廷一直密切的关注着内廷中皇帝的身体,终于在五月二十五日,隆庆紧急召集内阁三位大臣高拱,张居正和新入阁的高仪去乾清宫。在乾清宫见到的隆庆,已经奄奄一息,他躺在床上,旁边站着他的继承人,虚岁才十岁的皇长子朱翊钧。陈皇后和李贵妃坐在帷帘后面。皇帝,皇太子,皇后,贵妃,内阁大臣,司礼太监,他们聚集在一起,将要决定一个王朝的传承。
高拱等人强忍着悲痛,跪在了隆庆的床前,隆庆看到高拱,脸上逐渐有了一丝欣慰的神色,他挣扎从被子里伸出自己的手,想要去抓高拱,高拱连忙把自己的伸了过去,让隆庆抓住。隆庆紧紧握着高拱的手,缓缓的说:“以天下累先生!”
高拱再也忍不住,哭泣起来,隆庆挥手,让冯保宣读了自己的遗诏,遗诏有两份,一份给太子,以直白的口吻传达了自己对儿子最后的要求。还有一份,写给三位阁臣,任命他们为皇太子的顾命大臣。
当冯保将诏书读完,众人再也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悲痛,全都放声大哭,高拱强忍着泣声,边哭边对隆庆说:“臣等受皇上圣恩,誓死以报,太子虽然还年幼,但是祖宗法度都在,臣等一定竭尽所能,尽心辅佐,望皇上不要以后事为忧!”说完便痛苦失声,长号不止,旁边的皇后和贵妃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哭泣起来,李贵妃哭了一会,忍住哭泣,劝高拱等说,诸位先生国事要紧,还是要保重身体。三位内阁大臣在劝说之下,努力压制心中的悲痛,被太监们扶起来抬了出去,刚出乾清宫的大门,又忍不住放声痛哭。
第二天,昏迷了一天的隆庆皇帝撒手人寰,离开了他的大明王朝,他的臣子们对他极尽爱戴,听闻皇帝驾崩,像内阁大臣们一样,都痛哭流涕。这位精明的皇帝宽厚仁慈,他曾经非常喜欢吃驴肠,但是后来却禁止御膳房做这道菜,因为他觉得为自己吃一次驴肠就要杀一头驴实在于心不忍。他也很节俭,平时不怎么爱奢侈,知道外面的一盒糕点只要几文钱,他的遗诏要求所有的亲王宗室不要来京治丧,封疆大吏不准擅离职守,用最节省的方式举行了自己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