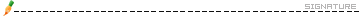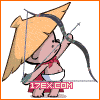兔歌
学校的西北角是一片墓地,我偷偷的才看到的,被全掘了开,棺材板散了落了一地。
我悚然。
下课时,大家都抱着书往回走,都从墓地旁路过,却没有人扒开路傍的林木往里望。我在想,他们知道那是墓么?不知道,那他们为什么不去看。
他们知道,如果这样,或许他们就是从里面出来的。那天天气很好,冷飕飕。
我又去墓地了,远远的找了棵树躲在后面,我知道,和我一起上课的他们,会回到这里,或者从这里去上课,所以我等着,我一定要找到证据,歪倒着的墓碑,棺材板散了落了一地,一定是爬出来时候的痕迹。
冷飕飕,我站在树后,静静的,我想,该出来了,所以才安静。果然,我听见有人在唱,从那些棺材板的缝隙中,又或者我的脑后。随着风吹来的方向,幽幽的却清晰。
大兔子病了,二兔子瞧;
三兔子买药,四兔子熬。
五兔子死了,六兔子抬。
七兔子挖坑,八兔子埋。
九兔子坐在地上哭起来,
十兔子问它为什么哭?
九兔子说,五兔子一去不回来。
他们在唱什么,是他们回来还是将要离开?五兔子一去不回来,兔子,这里埋得是兔子?不,他们就是兔子。我恍然了,难怪他们的眼睛都那么的通红,像涂着血一样,他们直勾勾的望着我,用他们那血红的眸子。
我逃一般的回来,我怕我也被染上,我的眸子是黑色的,他们说是黄绿色。怎么会是黄绿色呢?他们说,红色和黑色混合在一起就是黄绿色。我害怕,于是哭起来。我老早就知道,他们是有阴谋的,我的眸子终于不黑了。要保卫它,哪怕是黄绿色的。
我有一个问题,他们怎么变成人的。要脱皮的么?我知道这个方法,我很多次的梦到过,一夜一夜,他们唱着,然后用刀划破头皮,天灵盖上的头皮被拉出一条口子,流水般的水银就会顺着那个刀锋滑进,咕咕的血盖过毛发流动,流过身子,流过脚丫,流到那散落了一地棺材板的缝隙里,然后渗入龟裂的土地,于是慢慢地,你就能离开你的躯体,那密密的血管包裹着白皙的肌肉从那具皮囊中跳脱出来,在月亮下手舞足蹈。他们就是这么换上人皮的。我坚信是这样,没有什么可怀疑。
我要回去,我要找到那些浸入血中和土地黏糊在一起的兔皮,找到它们,然后点火,付之一炬。那个火,沾染上了黄泥,和那些干了的,暗红的血,一起燃烧起来,噼噼啪啪,那时红色焰火里,跳出一丝丝绿的闪光,就像他们的眼睛,可是,不,不,他们的瞳孔明明是血红的,绿色,那是我的眼睛……
我躲到那一片榆木树叶的背后,露出半个眼睛张望,我不敢两个眼睛都看出去,我怕这闪闪的绿色会把他们招来,他们就会围着我,围着我唱,五兔子一去不回来,五兔子一去不回来……我把眼睛收回来,在榆木叶后,我就看不到他们了。
这时,他们拍拍我的肩头,我想哀求他们,他们笑着,果然把我围起来,左右的晃动,像兔子一样的跳跃。他们又风一般的离了我,只是临走时对我说,你的眼睛像萤火虫一样。萤火虫,我似乎见过,屁股上闪着绿色的光,飘飘忽忽的,我知道了,他们发现了我,他们还是发现我了。我战战兢兢,看着他们跳着远去的影子,远处的坟地里冒起了一阵青烟,就绕在那根竹竿的上头,怎么也消不去。风好大,冷飕飕。
那根竹竿,我见过的,底下堆满了散落的棺材板,层层叠叠的垒起来,那是他们的祭祀方式,我早该想到,可我却没有,还在它的上面把那堆可恶的兔子皮烧掉了。这一定是信号,不一会儿,他们就全都知道了,他们会回来要他们的皮的,他们找不到,他们长着血红的眼睛,而我是绿色的,所以,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找到我。我该怎么办?
我要防备,布置得周周密密,特别要提高警惕,他们会跟我说,走,上课去啊。是啊,上课,谁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上课,他们不会去上课的。你见过兔子们上课么?他们是要叫我,叫我跟着他们。去那个坟地,他们终于要举行仪式了,我不就是很好的祭品么?哈哈哈,他们要下手了。周围都是他们,他们朝我喊,像训斥他们豢养的动物一样,快!不要磨蹭!
我要成祭品了,因为我是长着绿瞳孔的。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我只有跟着走,我逃不出去。对了,那堆烧焦了的兔毛,他们一定看见了,他们是像我来寻仇的。我要跑,我会被这群红眼睛的人给吃掉的,他们望着我,就用他们红红的眼睛,似乎在告诉我,烧吧烧吧,五兔子死了,六兔子抬。七兔子挖坑,八兔子埋。烧了的,还要还回来。他们是兔子啊。
我被推攘着,夹裹在他们之中,一点点朝那个方向去。我看见了那堆兔毛上烧起来了熊熊的火焰,我记得,我亲眼看着它们烧成灰的,这不可能,难道灰也是会烧起来的么?我瞪大了眼睛,想把那火焰看透,看看那跳动的烈焰背后,游荡的是什么。
他们突然放开了我,像四处散开来,又像汇合的水流一般,把那火堆围了起来。那一个个白色的躯体,疯狂的跳着,在我的眼中时现时无。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大兔子……二兔子……三兔子……六兔子……七兔子……十兔子……”“病了……死了……埋了……死了……埋了……埋了……”
我像被五花大绑了,只能呆呆地立在旁边,怎么也不能动。过了一会儿,那高高的火焰散出幽幽的绿色,那是我烧兔子毛时候的绿,在红红的跳焰中,那一丝的绿,是那么的碧,碧得晃人眼。他们不再跳了,可眼睛都直勾勾得看着那根竹竿,上面萦绕着未散尽的青烟,他们抱在一起,缓缓地唱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另一首曲子,那声音低到了土里,
大家小心翼翼,神明在我们的头顶
回家的路幽暗暗,我们手牵手
手牵手,我们就互相认得出
我们一起翻山越岭
我们一起穿过那沙沙响的树林
可它为什么沙沙地响
谁知道,为什么
……
他们的眼光黯淡下去,他们如同丢失了他们的魂魄,如贵妇人丢失了心爱的皮毛一般,一遍又一遍的低声念着,“它为什么沙沙地响,为什么,为什么……”那声音越来越低沉,回旋着,飞快的在周围扩散,那火也改变了跳动的方向,和着这一声声的念叨。他们眼里流出泪,那颗血眸子就被冲淡了,如鲜血般的泪水,洗刷着那血管包裹着的白色躯干,他们呜呜地哭着,我以为他们在祭祀他们的皮毛,被我烧掉的皮毛,于是他们只能整日套上人的皮,呵,他们想方设法换上人的皮,不就是想做人么?现在呢?现在呢?为什么他们终于可以不用脱下人皮,却哭得那么伤心。可恶的兔子,他们竟还不知足么!
不!我知道了,我突然知道了。一、二、三、四、五……一百、两百、三百、四百……这里有那么多的兔子啊,它们套上人皮,为它们的皮毛哭泣,那,失去了皮毛的人,一、二、三、四、五……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他们,在哪里?
它们是在祭祀他们的皮毛么?它们莫不是在祭祀它们的蜕变,这个仪式主角是谁?是我还是它们。它们的背后,火焰重新高高燃起,这千百双的眼睛为什么又如此通红,一转不转的全盯着我,它们,原来它们是要脱我的皮。
我四处张望,就如同被惊吓了,我那幽绿的眼神四处飘离,就如同熊熊烈火里的飞蛾,在火焰上翻飞,身上抖落的璘粉,落到火焰中那白亮的中心,然后啪——啪——几声作响,绽开出几朵碧绿的莲花,慢慢升腾起来。它们眼睛咪做一条缝,我于是愈发把眼睛瞪大。他们把头伸过来,我于是后退,退到不能再退。
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局。那天我才来,他们很好的,帮我提了行李。我住在学校的西南,那个地方叫桂庙,种满了郁郁森森的树,有零落的楼房,我穿梭在那些林荫小道中,有一天我才觉得奇怪,桂庙,这里没有桂树,也没有庙。
为什么没有庙?我问。于是他们笑起来,树上的鸟也跟着哈哈大笑,他们笑得岔了气,笑得趴在地上,捶着地板,流着眼泪,笑啊笑,怎么也不停,而笑声活进了眼泪流过地板,流进了墙角,便永远停在屋子里,不愿消散去。我坐在床上,夏天炎炎的热气,熏得我昏昏睡去,一阵风在窗口吹过的时候,我就听到了那些笑,从墙角里出来,顺着楼上渗下来的水,在墙壁上,沿着砖缝,然后到我的脚底。我跳着,一蹦一蹦的躲着,嚎叫(howl)起来,这嚎叫就如同我的眼睛,绿幽幽的,淹没在血红的瞳孔里,被一点点散开的笑盖了过去。
我跑出来,因为外面有大大的太阳,我要这热灼灼的阳光照耀在那见不得人的笑声上,从石灰缝里一点点爬出来的发霉的笑。我高高扬起头,直面太阳,去看那白晃晃的火球,就在那一刹那,我眺望见那根插在坟地里的竹竿,好远,我根本看不见的竹竿,但却一定是的,上面一圈青烟,还没有散。
我想着的时候,它们就把脸挤了出来,笑着跟我说,桂庙。知道么?这青烟散不去,于是我们被它召唤来。散不去。你为什么不去桂庙里祷告,不祷告是永远散不去的。它是桂树啊,我们是兔子呢。你看,头顶的月亮明晃晃,比那太阳还要亮了。
我的妈妈杀了我,
我的爸爸在吃我,
我的兄弟和姊妹坐在餐桌底,
捡起我的骨头,
埋了它们,
埋到冰冷的石碑下
他们在我面前停下来,他们的嘴一张一合,舌头却僵硬得动弹不了,从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声音,越来越沉闷,从喉咙到了他们的胃里,又到大肠里,从他们的肚子中回荡出来。
是他们!我听得出来。我才来的时候,他们都很好。有一天,甲他买袜子去了,很久才回来了,他笑着,背着手。我问,袜子呢?他便跳了跳,放开手,手上套着袜子,那双格子的袜子,雪白铺着血红的格子,他把手并起来,高高举过头,对我说,你看,像不像兔子。
我还记得,乙他回来时,喝得醉醺醺,一头扎进床里,夜半,月亮照进屋子,我被人推醒,是他,瞪大着的眼睛,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吃鸡去了,来了一只兔子,它居然会啃骨头,啃骨头,它把那些鸡翅全吃了啊。
现在我分明听见,是他们的声音,从兔子们的肚子里。一声又一声,你看,像不像兔子。你知道吗,它居然会啃骨头,它把那些鸡翅全吃了啊。
是人,那些失去了皮毛的人,我知道了,全在它们的肚子里,在它们的胃里和大肠里。剩下了的骨头,早就被捡起,埋了它们,在那些冰冷的石碑下。
我确定一切都在发生,从前我从来不这样肯定。丙他挂着他的小书包,飞一样冲到我面前,指着天,你看啊,太阳被遮起来了。那一刻,我便确定了。那天的太阳被盖缺了一个角,颓唐的挂在天上,我的周围便一阵欢呼,他们说,那是月亮的影子。我小心的溜走,月亮能盖住太阳的么,况且,那是影子。后来慢慢太阳又全了,但我知道,这是让我不起疑,故意的。他们怎么能骗过我呢,以前的那个太阳早被他们换了。
我是听到了他们的秘密,所以他们才要把我祭祀给了他们的神。我看到过五兔子蹲在路中间,他在唱歌呢,
红花开,红花落
红花落在她的鼻头
如雪的肌肤,如血的花
鸟儿们喜欢这红花
于是它们衔走了她的鼻子
我知道兔子们是不单独唱歌的,它们总是聚集在一起,可五兔子就像这样唱的,一个人,蹲在路中间。后来它果真死了。我死一只兔,你死一个人,这是他们的约定。
你拍一,我拍一
一只兔子做寿衣
你拍二,我拍二
两只兔子劈棺材
你拍三,我拍三
挖坟一挖一十三
你拍四,我拍四
……
天色终于暗下来了,树上唧唧喳喳的鸟儿,回到了它们的巢穴,草丛里跌跌撞撞的虫子们,也钻进了泥土中,它们明天又会出来的。我呢?
他们知道。他们挠着脑袋,不安地跳动着,眼睛却不愿意从我身上有丝毫的偏离。他们是在等着什么,如果不是的话,我可能早就成了灰,和那堆兔子皮一样,被扔进那簇火里,变作青烟。我想,我会容易打发一些的,我不埋怨,也不会聒噪,我随着风就消失了,也不会围着那棵光秃秃毫无生气的竹竿。
我突然想笑。想蹦起来。想跟着树林那沙沙声唱起歌。我就要死了,他们是刽子手啊,可他们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布置这么一个精密的局呢?兔子也会啃骨头的,他们一拥而上,我就死了。难道不嫌麻烦么?我知道,我的骨头依旧会被埋入那些冰冷入骨的石碑下,只有那些还留下点零碎的灵魂的烂肉,被它们收入腹中,还哀怨哼着小曲。太阳已经下去了,那颗令人恶心的假太阳,它再也不用伪装的升起来骗我,我束手就擒了。
它们给了我一把刀,我先挖去我的双眼,那绿幽幽的眼睛本不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欢呼着,跳起舞蹈,我的那双眼睛被它们踩在脚底,尘土蒙蔽了它。
我终于哈哈大笑了,举起我的双手,撩开浓密的头发,让那把刀划破了我的头皮。留出来的血渗出了发根,流入我凹陷的眼眶,然后开始凝结。
明晃晃的月亮从西边慢慢升起来,它耀眼的光芒,穿过周围浓密的灌木,透过稀疏的树枝,照在这方土地上。它们对着月亮升起的地方下跪膜拜,于是月色更加分明,它一点点的爬上了我的身体,让我感受着光的重量,最后它照到了那柄刀上,刀尖还嵌在我的头皮里,血向外流着。
那刀就化了,化作银白色的流质,顺着那道划开的口子,压进我的身躯,然后一点一点纵深,我听到皮肉分离时那汩汩的声音,从头顶开始,到脖,到胸,再到腹,再往下。
那群活蹦乱跳的兔子,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笑了,却回过头,不再看我,他们说,孩子,出来吧。
于是一只颤巍巍小兔子从兔群后面闪出身影,用自己那双血红色如豆粒般的眼睛,注视着前面的我,然后它问道,这就是我的皮么?
2007.4 5—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