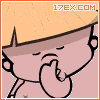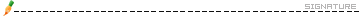十九岁那年,我所在的C城,下了一场七度的雨。
夏站在雨中,跟我讲起了他初中的爱情。他说他喜欢上一个叫汀的女孩,已经忘记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只知道会在夜中不经意间想起她。
那是一个很弱小的女孩,常常在教室里生病。夏曾经抱着她,从教室跑到校医室;校医室关门了,他又抱着她跑到离学校最近的医院。
他说他愿意抱着她一直跑下去,即使全世界只有一所医院,即使唯一的这所医院就在西半球。
汀没有听到夏的这段话,但她还是做了夏的女朋友,也许是出于感动,也许是需要有人关怀……
这是故事的起点,而终点其实也不远。像大多数人的爱情一样,在中考过后的那个宁静的夏天,桉树上的知了为夏和汀之间的爱情唱了一首荒凉的挽歌。
夏说,在汀走的那一天,他抱着吉他给她唱了一首歌,那也正是初中的毕业聚会。那次聚会有太多的眼泪,汀也同样感动地在哭。可是,最后的最后,汀还是离开了夏。
夏笑着问,是不是女人是即情的动物,而我们男人是长情的,除了某些花花公子?
后来的岁月,夏一直单身。他喜欢音乐,长得不高,有着颓败的笑容,偶尔会在C城的街头弹唱一首,等着城管来赶他走。夏说,他弹得最好的是D调,却无法弹好C调,就像无法守护住自己的爱情一样。
我们就这样,两个人,在C城的一中过简单的日子。记忆里的一中,有绵延不尽的木棉,有吹过湖面的好风以及青春的味道。
夏睡在我的上铺,夜不能寐的时候,就从上面滑下来,叫醒我一起聊天,一直聊到深夜三四点。偶尔会有咖啡相伴,冲在一次性的纸杯里。他一直不停地讲,而我却是个耐心的孩子,静静地听,频频地点头。
他说他的心中一直留有汀的位置;他说他怕汀再次晕倒的时候再没有人有勇气抱着她满城飞跑,即使这个世界有再多的医院,再多的医生,也无法为汀找到她最合适的。
夏说,汀会药物过敏,有很多很多的药不能接触,像注射用的肾上腺素、抵噻咪松和口服的三七粉,甚至那种有蓝色糖衣外壳的“感冒通”也不能吃。他很耐心地记住这些药的名字,记得比化学公式还牢固。
说着说着,他会突然停下来,很无助很乏力的一个孩子。
他一直没有问起我的故事,或许在等我开口,而我也一直乏于去讲述心中的疼痛。只是,他说他故事的时候,我也会想我的女孩。我将她的名字设成手机屏保,想她的时候,便看看手机屏幕上那三个字,“我之X”。
夏一直无法走出汀的阴影,直到遇到了冉冉。
冉冉是个喜欢画画的女孩,她常常给一个杂志社寄漫画。她说画画比恋爱还要甜,她说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建最美的房屋,画长长的海岸线,懒洋洋的阳光以及慵散的青春,还有青春里的风车……
C城的一中,有个安静的湖,叫三生湖。夏和冉冉便在这里相遇相识,一个爱好音乐,一个爱好美术,我想,这是不是上帝故意的安排呢?期待着,期待他们的幸福。
夏带着冉冉去“风吹岩”画飞鸟飞过低矮的城堡,飞过远处的房屋;而冉冉则为夏求了一个“平安符”。他们坐在那块高高的岩石上背靠背聊着话,述说着关于“风吹岩”的古老传说。他们有一辆四轮的脚踏车,说要踩着去环绕C城。
夏说他已经爱上了冉冉,关于汀的一切,只会偶尔地使他感到心痛,感动遗憾。我点了点头,他继续说,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天,他会为冉冉在三生湖畔高声地唱一首歌,抱着吉他,边弹边唱,唱那首《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只能一再地让你相信我
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在你身后
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你和你的爱情在四季传唱
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
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
夏说要带着冉冉去流浪,去荒野流离。
我说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为我的女孩在彼岸的夜晚放一场烟花,我要让她看到我心中的寂寞。
那像风车一样旋转的高三,不紧不慢;时光漫过指尖,花开花落,一切在沙沙笔声中消减。冉冉和夏却洒脱地过着他们的生活,仿佛以一种不羁的方式去抗拒成长的代价。我站在远处观望,偶尔也会与他们狂欢地走过。
那时候的天很蓝很蓝,那时候的我们快乐而又无邪。
只是,到了那么的一晚,空再次滑下床来与我夜聊时,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不快乐。
夏问我,有没有想到死亡?
没有,我一直很好。
有没有想到自杀,你知道人死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痛的吗?
不知道。——我依然对着夏摇了摇头,但我确实吃了一惊,我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问。也许他一直很痛苦;也许,那往日的笑容是借以掩盖心痛的符号。
他接着说,是从心开始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在一瞬间想到遗憾,想到绝望,想到有些人还没有爱够,或者再也无能为力去爱。然后,心就会狠狠地疼,狠狠地痛,在心痛中死去。
夏还说,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选择自杀吗?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痛得无法再忍受,比肌肤之痛还要痛。他们无法在心痛的折磨下一天死一次。所以,他们选择在一次心痛和一次肌肤之痛的结合下一生只死一次。
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晚是夏以前那位汀的生日。他说他在那一晚碰巧梦到了汀,他感到很无助很痛苦。
“一切是那么地真实和自然,仿佛就在昨天发生。我梦到她陪着我一起走,走很长很长的路,那条路仿佛没有尽头。那时,我多么地高兴,多么地幸福,我在梦中笑……可是,当我醒来,我却发现自己是在做梦。那种落差,你懂吗?周围很黑,夜很深,我发现那一切其实已经离我很远很远,她已不在我身边。三年一梦,多么地真切,我的心很痛很痛,我很伤很伤。”
“你不是说你已经忘记了汀,只爱冉冉吗?”
“嗯,但我为什么还会梦到汀呢?而且那么地真,那么地自然,我好有罪恶感。”
有些时候,就这样子,当你以为你已经彻底地忘干净一个人的时候,你还是会在某个夜里很巧合地想起。你说你已不爱她,说得那么地坚定,但那份曾经有过的情怀还是会在你不设防的时候击败你,让你泪如雨下。
我告诉冉冉,夏过得不快乐,你要好好照顾他。
她定定地看着我,咬了咬下唇,然后点了点头,塞给我一颗“上好佳”果糖,便走了。
两个月后,我们三个人去中信海滩游玩。夏和冉冉在平地上踩着他们的四轮脚踏车,而我一个人在沙滩上看海,偶尔会将一块又一块的贝壳扔向远方,看着溅起的浪花以及远处安静的灯塔。
我在沙滩上一次又一次地写着X的名字,写完就抹掉,抹完又写,恨不得让整个沙滩都写满我的孤独。
“圣,你在干什么哦?”冉冉从远处跑过来,我来不及擦掉沙滩上的名字,被她看到了。
她蹲下来,问我:“你还在想着那个女孩,想着X?”
“嗯”,我点了点头,接着说,“我刚才还在想,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呢?”
“傻的你,我才不会有什么信仰,只信仰蒙牛的三色雪糕和上好佳的果糖,要青苹果味的。不是青苹果味就不要。你呢,你信仰基督?”
“没有。如果真有信仰,我想,我只会信仰我爱的女孩,一生不变。”
“你去死啊,花痴狂,每天都说这些话”,冉冉好像又气又好笑的样子,说着说着还站起来用手中的包狂欧我的头,“想多会疯的,再说这些话,把你扔进大海喂鲨鱼。”
我蹲在地上,用双手抱着头,久久不敢动弹。她骂完打完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才又静静地返回来,给了我一颗“上好佳”的果糖,说:“走啦,花痴,去找阿夏啊,他在那边等我们呢。我们一起去玩拍手掌哦。”
她让我摊开双手放在夏的手掌下,我微微抖动双手,趁其不备的时候狠狠地打夏的手背。我们就这样,输输赢赢,相互打着对方的手背。而冉冉则在一旁不停地笑,笑弯了腰。
冉冉有两个深深的酒窝,笑起来很好看,很甜的感觉。所以,夏常常因为看冉冉的酒窝而走了神,我则狂打他手背。
后来,我们玩“三人四足”,夏的右脚系着冉冉的左脚,冉冉的右脚系着我的左脚,三个人捆在一起,肩搭肩,“一二一二”地向前走……
那时候的我们,多么地快乐。金色的海滩,落日的余辉,我们的笑声,还有潮退的声音,一切安详如画,有着淡淡的疲惫,淡淡的幸福。我们三个人,四只脚,沿着海岸线走,走到最后的时候,错乱了脚步,软绵绵地倒在沙滩上,笑成一片。
我们倒仰着头,看身后歪歪斜斜的脚印,大小不一,那是一串串幸福的符号,刻画着青春的快乐。
夏在那一夜站在沙滩上,向着大海弹唱着一首歌,叫《蓝莲花》,他很瘦很瘦,有着许巍一样的面孔和歌喉,沧桑落寞: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地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地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
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而旁边的篝火跳跃着,冉冉看看夏,又看看我……我们一起被音乐所击败,三个人泪光闪闪。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