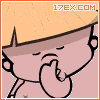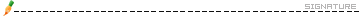这是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已穷得和小良在宿舍里煮饭过日子。小米加大米,再加小白菜,我相信我的厨艺不错。这也便是我在这个冬天里仅有的幸福。在每个凌晨的三点钟,因想念一个人而无法入睡时,便起来煮粥喝。或许,心灵上的空虚有时可以用米饭来充实。
已经忘却了想念她的理由和意义,或许也不曾知道,正如米饭之于我的意义。只知道,在这个渐微寒冷的季节,需要用她的记忆来温暖我的手脚。我所路过的生命,不巧遇到了她,每一夜都如歌一般伤感。谁也无法告诉我,走入的是一条死胡同,还是路过一个冬天的死角。
平安夜的那一晚,站在红榴斋听烟花绽放的声音,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样,轻轻地,狠狠地。我便在那些寂寞的声音中发出最后一条短信:“今晚你晚点睡,陪多我一点,好吗?”接着,在寂静中等待回音。可是,没有,一个世纪的安静仿佛在延长。那一夜,风在吹;那一夜,我多么地寂寞。我说,如果能爬上屋顶,我一定会在屋顶上行走,等待星星掉下来,等待一个人的发香从远方飘来。可是,终究尘归尘,土归土,我的幻想在这个冬天化成灰。
于是,一个人看电影,《如果爱》,那些化做雪花的眼泪,纷纷扬扬,铺洒着镜头,这个冬天似乎不曾有过安慰。我想,死结,便是爱与恨两条线的纠结;死角,便是爱与恨两堵墙的交叠。我从那个死角路过,却没有躲在那避风。所以,我注定要哀伤,正如蛇注定用肚皮走路。
十九岁之前,我坚信爱情的海枯石烂;而十九岁之后,我已渐渐相信爱情的沧海桑田。所谓的爱情,或许就像西北穆斯林的羊肉烧烤,一串又一串,吃了就被扔。很少有人会在这冬日沏一泡工夫茶,耐心等待一个人。多少单纯的日子,多少透明的幸福已成为多少人的记忆。可我依然会想念远方,想念故乡的黄昏。
曾经在华强北购物的时候,恍惚地看到一个女孩的神情与她是多么地相似。我肆无忌惮地看着那个陌生人,直到她走近,才知道她终究不是我的那个她。那样的一种落寞谁会懂?在凌晨写日记时,会痛苦地趴在写字台上不停地回忆她的容颜,恐怕有一天会模糊了她的样子。而她是否依然记得我的样子?或许忘了,或许记起我的时候,我已消瘦得让她认不出来。没有谁敢保证十年后,当在街角遇到爱过的人时,依然会认得出,依然会有当日的深情。而故乡的木棉已凋尽的时候,你和我,或许也苍老得说不出话。
于是,黄昏,木棉,还有年少时的风,以及我这个2005年的冬天,都成了永世陪伴我们的殉葬品。所有的爱与恨,所有的死角,因为城墙的瘫痪而随风飘散。那堵刻着记忆的墙,书画的不再是你的容颜。只有我的这些文字,依然可以记载着我曾经的伤痛和你的美丽,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2005年,在这最后的一天,回乡的日子也一天天逼近。朋友说,是该回一中去看看的时候了。可我不愿去,不是我不爱一中,我爱它爱得心都发痛,只是我怕记忆的洪流会使我喘不过气来,我胆怯得不敢去面对我爱的母校,正如我胆怯得不敢去面对我爱的人。人去楼空,最怕的是楼去人也空,物非人也非;最怕的是我的忧伤无法掩盖得完整,让你看了,也瞎让你操心。在这个冬天的死角,我就这样,静静地路过,不去回眸,不去转身,拿起自己的手掌,看手中的掌纹那一幅古老的爱情地图走自己的路。
(2005.12.31)